如此寂静的悲伤和疼痛
——读杨子诗集《胭脂》
徐庄
《胭脂》是杨子的第二本诗集。单从书名去揣测,读者恐怕要遭受不小的打击,因为在这里,胭脂代表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。
我所认识的杨子,是一位本质上的诗人。二十多年来,他一直在安静地写诗,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,从未间断。他的抽屉里静静地躺着几百首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作品。可以说,一开始他就把自己放在了诗歌的本位:一种寂静的美的流淌,一种血管深处的呐喊和歌唱。
读这本《胭脂》,我几欲泪下。如此寂静的悲伤和疼痛,其力量要大过千军万马。当我发短信告诉他我的感受时,他的回复是,“以后不这么写了。”
《胭脂》写了十三年,从西北到东南,从新疆到广东。高架桥、玻璃幕墙、死去的河流、民工、妓女、上班族、梦魇、焦灼、悲伤的月亮和沦落的月亮,是这里面的主要内容。如果把心胸放宽一点,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本当代《诗经》。不同的是,《诗经》里的那种民风淳朴、温柔敦厚,在这里变成了荒诞和腐烂、异化和碾碎,人与物,天与地,皆遭荼毒。
这中间,杨子始终是不安的,他像一个孩子被惊吓得离开了躯体的魂魄那样,在黑暗中飘荡,惊悚地打量着这个世界;又像是《神曲》里的但丁,过了一关又一关,与鬼神谈话,打探世人的出路;又像是唐·吉诃德,总是忍不住鲁莽地举起自己的枪矛。
在新疆的乡下,他看到一对酒鬼父子:“父亲不停地笑/他去追一只受伤的乌鸦/跌倒了,坐在地上不起来/儿子跑到公社大院里/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/找一个名叫金花的姑娘”(《酒鬼父子》)。这样的场景,是他刚刚抵达广州时对于新疆的记忆。这时,他和这个世界偶尔还能相互点头,微笑,不全是剑拔弩张。
很快,他看到和听到的都完全不一样了:“卑贱的穷人/好像被看不见的靴子踢着/在尘埃中打滚”,“很多人来不及洗脸/很多人不脱袜子就躺倒了床上/很多人把做爱的时间腾出来/去谈合同,去做假帐,去陪客人洗脚”,“一个清洁工在打捞河上漂浮的垃圾/像是给死者整容”。他听到这个城市发出古怪的窃窃私语:“亏损算谁的/年终奖怎么办/谁替我供楼/老婆不答应/儿女不答应/那小妞也不答应”(《惊慌的城市》)。
挖掘机、摩天大楼、夜总会、码头、证券交易所、闪着粉红灯光的发廊、穿防弹背心的警察,这些膨胀的词汇,这些寓意深刻的镜像,加上这个纵横交错的下水道般的迷宫城市,终于把他搅晕了。他开始低烧、头疼、不能自主地在深夜里疾走。
《胭脂》的后半部,你总能感到他在不停地疾走,在深夜,无法停歇。他像是急于找到一样东西。那轮被古代诗人赞颂了千百年的月亮,高悬在怪兽般的高架桥上空,令他茫然不解:“这么浑圆的月亮,/ 这么娇嫩的黄色,/ 我的眼睛感受不到 / 一点点愉悦”,而“八百万人口的大城/只有两座教堂和一座寺庙/供人下跪,忏悔,以泪洗面”,“谁来诊治灵魂的感冒,咳嗽和坏血病呢”?
当发出这样的疑问时,无可避免地,他成了整个人间的神经,人世每一个细胞的跳动,都会让他战栗。他陷入越来越剧烈的疼痛。
这时候,和在新疆写那组《说给石头听》一样,他仍然不能面对面地向人倾诉。他给远在新疆察布查尔的一个老朋友写信(《新年写给阿苏的信》),谈起十多年前的一次远游,谈起美好的郊游、舞会和白杨树上的一千只乌鸦,他担心朋友们离开后这位朋友的处境,他向这位老友打听那个边疆小镇:“那些老萨满早已死了吧?/他们的脚心有没有刀梯留下的伤口?”还向朋友汇报了他现在的情况,既有感伤,也有愤怒,以及对于得胜的物质世界的轻蔑。有一次,他借用契诃夫写给妹妹的书信,来折射自己的心境,“我正走进一个怪异的世界。/这里的苍蝇很大……”。他一边潜入这个疯狂的世界的内部,对它进行深度的观察和描摹,一边又抗拒着疯癫的洪流,“我决定变成一个宁静的人,/变成月光下的池塘,/变成宁静本身,/像一粒小石子,/裹在噪音的大衣里,/继续漫无目的的旅行”。
很显然,这都是不切实际的。他经由的地方,就是我们的血肉,甚至骨髓。广州沸腾的大街和污秽的下水道,已经挺进到新疆,新疆的蒙面大盗也藏匿在广州。他,和所有正在疼痛的,是同一根被拉紧的神经。在我们的烂肉还没有剔除干净的时候,他只能疼痛。
《胭脂》是一部疼痛之歌。在《胭脂》这首诗里,他写道:“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啊,/八百万人做着一模一样的梦:/钱,钱,钱!/而钱不过是抹在/他们死去的生活上的/胭脂。”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,但我宁愿把这“胭脂”看作是疼痛和羞耻之色。当我们不再感到疼痛和羞耻,只能说明我们已成僵尸。
《胭脂》 杨子著 海风出版社 2007年7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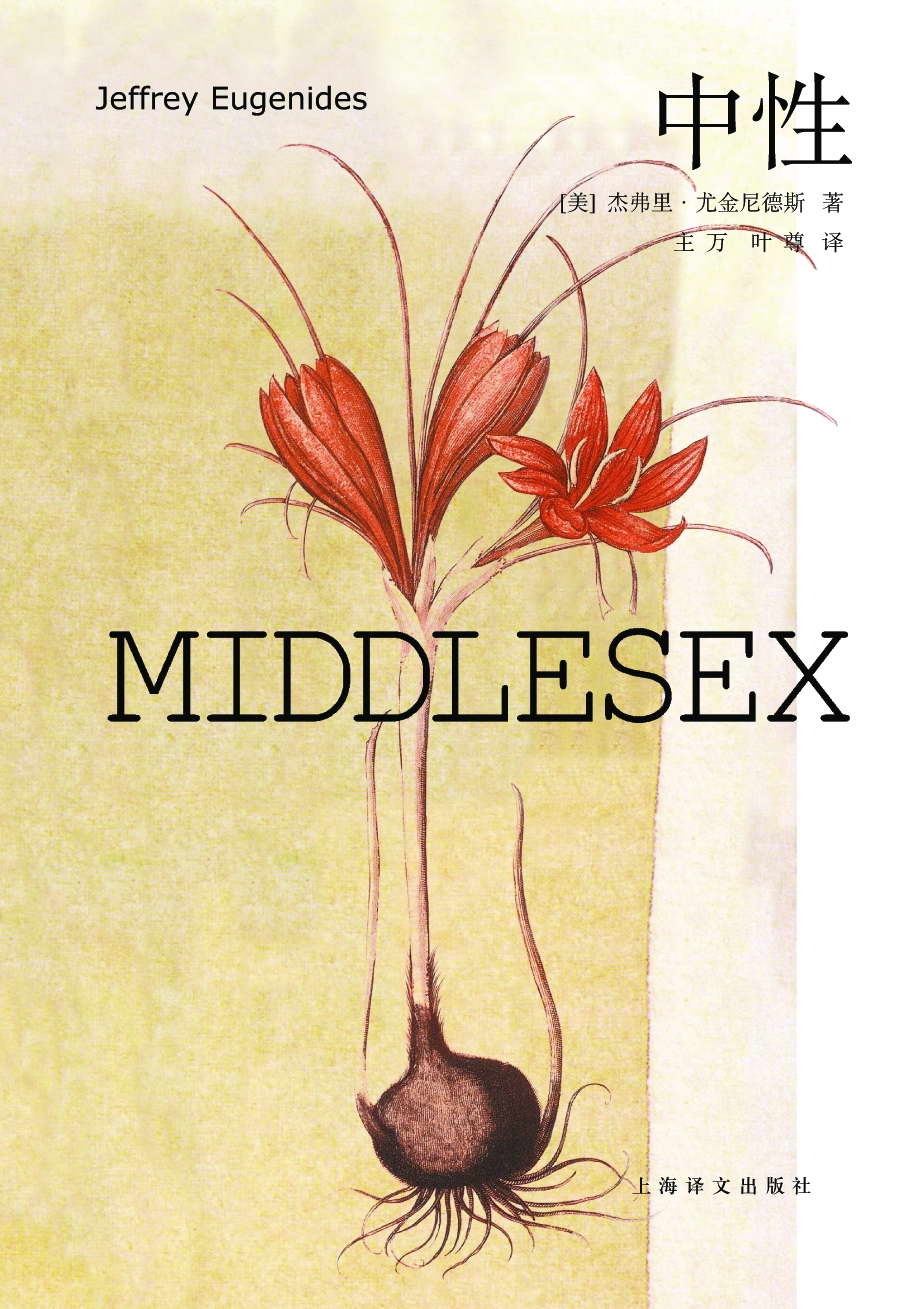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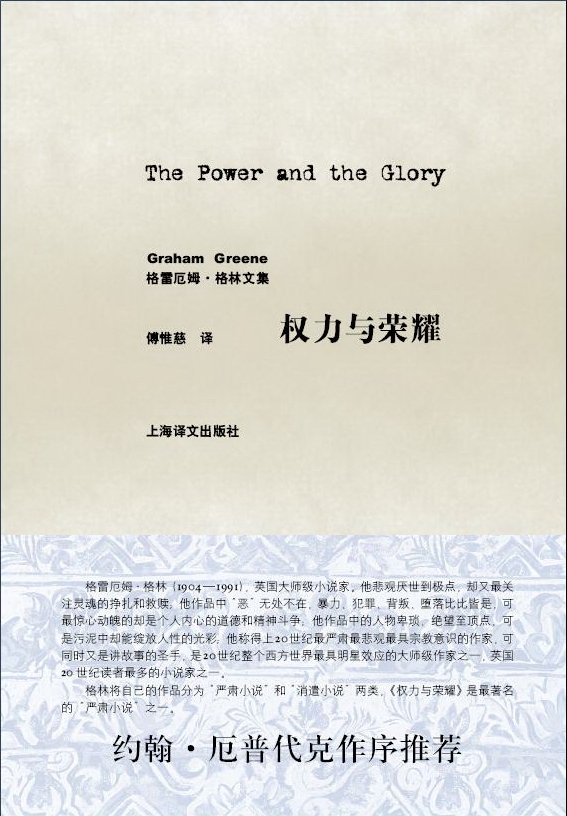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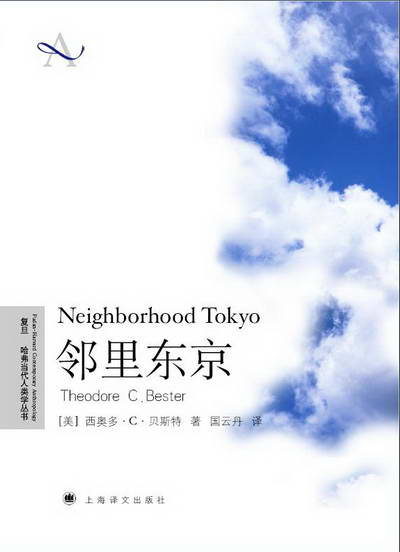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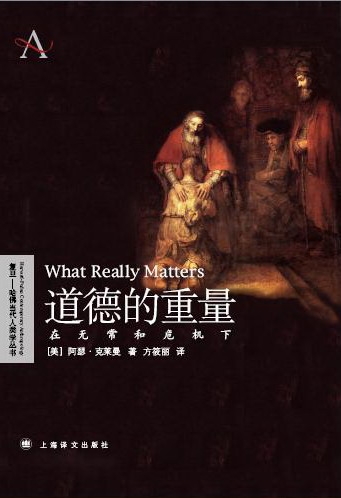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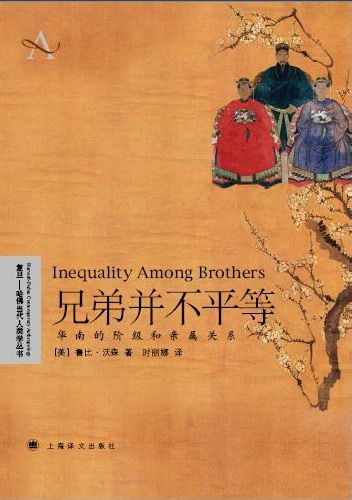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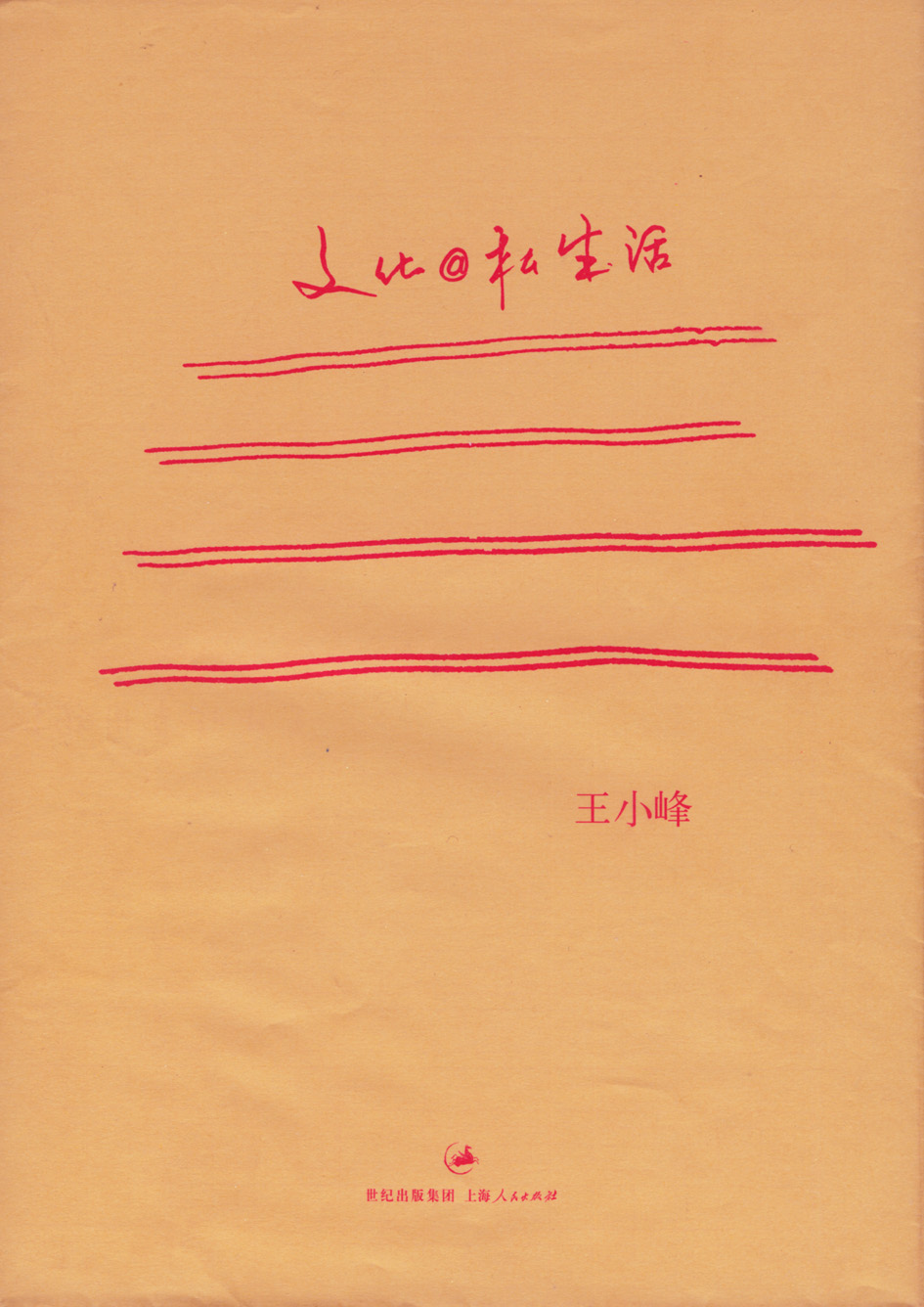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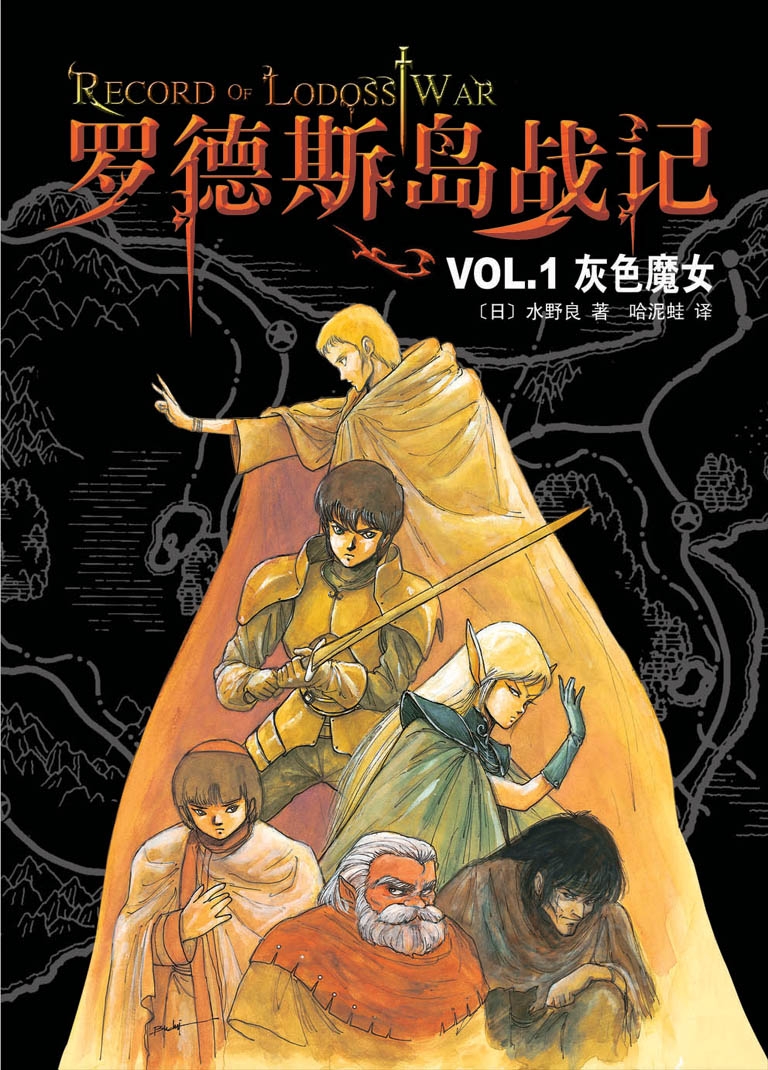
近期评论